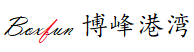我张大了嘴巴久久不能合拢--她居然会想到这样一种说辞!
事情来得太过出人意料,以至于一瞬间我丧失了判断力,我不知道我是应该表示感谢还是应当立即指出这种说法的荒谬.我毫不怀疑她这样做是基于一种高尚的动机--她试图拯救我,但是为了这种高尚的动机就编造一个全无事实根据的理由,这值得推崇吗?她这样自说自话其结果将置我于何地?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个姑娘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说出这样的话,其背负的心理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做出的牺牲也同样是惊人的,我能够指责她吗?
顾蕾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响,静待我的反应.
我正在思考该如何反应时手被烟蒂烫了一下,我赶紧把它在烟灰缸里掐灭,同时捋清了思路,耐心地指出:"其实,我不过是问你如何知道我去了乡下,你只要告诉我老强的电话不就清楚了,干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顾蕾仿佛受了某种委屈,眼圈有些红了,眼眶里的泪滴呼之欲出,她突然用哽咽的语调嚷了起来:"我就是想告诉你,是我傻,都是我不好,行了吗?"泪水终于淌了出来,她哭了.
我极力保持耐心,委婉地劝慰:"顾蕾你这是何必呢?我没有说你傻,也没有说你不好,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欠缺周详的考虑,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你看,你说我们快结婚了,这分明是无中生有嘛,现在我回来了,为了我不被再次下放起见,也为了你的声誉起见,我们就得结婚,可我们可能结婚吗?我们不过才见过几次面,了解都谈不上,感情就更谈不上了,我刚才吃饭时说我喜欢你,你也清楚那不过是气话,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真的喜欢你,难道你也喜欢我吗?你也不可能真地就喜……"
我正打算替她作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她插话了.
她呜咽着说:"可我真的喜欢你."说完抬起泪眼望着我,幽怨的眼神象是在告别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亲人.
我的确可以感觉到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胸膛,它在我体内迅速炸开,炸得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我脆弱的心脏根本无法承载这个夜里发生的如此数量众多的意外,我崩溃了.
我觉得我陡然间透析了事情的全部脉络.
我终于按捺不住地起身咆哮了起来:"得了,顾蕾,我终于明白了,我他妈的完全是中了你们一家的圈套,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局长的女儿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喜欢我?你少来,你休想拉拢我,我明天就去揭发检举你老子和你哥哥,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能把我怎么样,告诉你我蒋众顶天立地是条汉子,谁要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我也让他好不了!"
我的眼神一定红得吓人,我完全忽略了顾蕾惨白的脸色.
我接着说:"我不稀罕谁的同情谁的可怜,更不需要谁的帮助,我自己的事自己应付得了!"然后摔门而去.
我推开了局党委办公室的门.
刚刚上班没多一会儿,局党委副书记李大姐还在静静的品她刚沏好的茶.见到我进来,吃了一惊,问:"有事吗?小蒋?"
我点点头,坐到她面前,虎着脸说:"关于安华那件事,我有些情况想反映."
我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安华公司引进项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李大姐作了汇报,其间掺杂引用了不少老强的精辟分析,我希望能够唤起李大姐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李大姐听毕我的陈辞,不紧不慢的喝了一口茶,说:"关于安华这件事,前些时候公司里的确流传着些风言风语,也有人写来了检举信,局党委很重视,立即着手进行了调查,事实证明那些传言和检举信里的东西都属子虚乌有,顾局长是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们不相信他会背离原则,事实也证明他是清白的,无愧于一个老党员的形象.小蒋你能这样主动地向组织上汇报情况,用意是好的,值得鼓励,不过为了消除影响嘛,安华这件事嘛,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好吗?"
我越听越是心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轻描淡写地就将这件事过去了?我不甘心,气愤地反问:"请问组织上是怎么调查的?作为可行性报告的作者,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什么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李大姐脸上露出了不悦,但仍旧语重心长地说:"小蒋啊,你还太年轻,有些事不是冲动就解决得了的,这件事组织上已经作出了决定,难道你不相信组织吗?再这样纠缠下去,对你的前途会有不利的影响,听我的劝,不要再提了."
威胁!完全是无耻的威胁!拿我的前途来威胁我,想不到平日待人热情的李大姐竟也会同那些人沆瀣一气!事情已经很明显了,组织上已经有了决定,虽然什么叫组织我还没有搞清楚,可是组织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切断了我的退路.我明白再说下去只会越说越僵,于是冷笑着起身,离开了党委办公室.
回我自己办公室的路上,一个年纪差不多平时挺熟的同事拦住了我,神秘兮兮地问:"听说你要做局长的女婿了,是真的吗?"
我一把推开他,大声怒吼:"滚!少他妈胡说八道!"
我想: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能以这样惊人的速度传播开去呢?
老周假装没有看见我进来,埋头看报.
我乐得清净,生怕他也问我局长女婿的问题,赶忙拽过一张报纸,装做用心地读了起来.
电话铃响,老周拿起听了一下,递给我,我接了过来,电话里的声音有点陌生,陌生的声音说:"蒋众吗?我是顾泓,我在楼下等你,你下来一趟."
是顾蕾的哥哥,我同他曾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写这份该死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时候,他请我和科长在市中心一间号称本市第一快刀的海鲜酒楼里吃饭,当时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澳洲龙虾和象拔蚌身上,没有过多注意到这位春风得意的局长公子,想不到他今天竟会找上门来.这明摆着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冷笑着放下电话,心里激荡着一种战士奔赴沙场的慷慨豪迈.
办公楼前停着一辆黑色本田,我走出楼门的时候,它的车笛很不礼貌地鸣叫了一声,我将双手插在裤兜里,压抑着满心的不快慢慢踱了过去.本田背对着我趴在那里一动不动,黑色的太阳膜遮住了车厢内的一切,凭添了几丝神秘.当我靠近的时候,它的前门被人无声地推开了,车里的人用一种命令的腔调抛出两个字:"上来!"
驾驶员座上坐着顾泓,戴着一付深色的太阳镜.车厢内光线暗淡,我实在看不出有戴着太阳镜的必要,"妈的,玩酷!"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声.
他甚至没有扭头看我,只是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根三五,然后把烟盒连同一只法国产的督朋火机递了过来.我老实不客气抽出一只点燃,督朋火机发出的那声清脆的响声令我对它爱不释手.
顾泓吸了两口烟,低沉着嗓子说:"我今天找你不是为了安华的事."这个开场白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动声色,静静地抽烟.他接着说:"昨天半夜顾蕾跑到我这儿哭了一晚上,她不肯告诉我原因,我想或许你知道."
我拿烟的手抖了一下.原来顾蕾在我离开后去了他哥哥那儿,想到她居然哭了一晚上,我产生了一丝内疚,但这丝内疚在我脑海中稍纵即逝,旋即为愤怒所替代,我冷冷地回答:"你找错人了,我不知道."
顾泓没有看我,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依旧用低沉的嗓音说:"小子,你掂掂自己的分量,你是不是还没被山沟里的蚊子叮够?安华的账我还没有跟你算完,要不是我妹妹你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我说话.我只有这一个妹妹,从小我就很疼她,我从没有见她象昨天晚上那样伤心过,我希望她一辈子都快乐,所以我今天来要听你说一句话,我要你保证今后永远不要让她再见到你,怎么样?如果你答应,安华的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我被他的起初的几句话所激怒,他最后几句使我着实吃了一惊,想不到他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本来我是不打算和顾蕾再见面了的,因为和顾蕾的相识根本就是阴差阳错,而由这种相识所派生出的种种啼笑皆非的后果已经令我穷于应付,但是见面也好,不见面也好,我认为这只能由我自己决定,尤其是听到他最后一句明显带有要挟色彩的条件,我更加觉得难以屈服认从.
我将烟头扔出车外,认真地说:"顾经理,你高估了我的能量,我的存在并不会左右任何人的喜怒哀乐,至于我们是否不再见面,这只有我和你的妹妹能够决定,与他人无关,安华的事我问心无愧,它既然已经发生,我想任何人都无权抹杀它的存在,谢谢你的烟,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要走了."
顾泓转过身,缓缓摘掉太阳镜,我看见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说:"小子,你在找死!"我说:"我早就在找死,你才知道么?!"
我翻出思真的电话,拿起了话筒,思真柔美的声音仿佛带着雨后的清新令我心情一振,暂时忘掉了适才的不快.问明是我之后,她说:"昨天真不好意思,那么匆匆的告辞,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怎么会呢?我一直担心那家小店破破烂烂的桌椅会让你记恨我呢,今天晚上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赔罪,怎么样?"我诚恳地发出邀请.
思真嗫嚅着,"这……你不是……我想你应该去约……"
我打断她:"思真,这件事我要向你道歉,我知道顾蕾是你的朋友,我昨天的玩笑开得实在太过了,不过我发誓我从一开始诚心邀请的就只是你,一直到现在,主角都是你,昨天的事是我不好,希望你可以谅解."
"可是,你这样是不是对顾….顾蕾太不公平了,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那你可把她伤得太重了,你应该去向她道歉,我……"
思真这样替顾蕾着想令我感动,"昨天的事的确是我不好,你走后,我已经把事情跟她解释清楚了,并且道了歉,而且昨天,你也见到了,顾蕾也有过分的地方,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错."
思真仍旧有些忧郁,"可是不管怎么说,你昨天那样做还是有些过分,我想……"
我斩钉截铁地说:"思真,你一定要来,我有些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雨,雨丝如织,浇得地面湿滑得象蘸水的绒垫.
思真最后答应了我的邀请.下班后我急匆匆回到宿舍换了一身衣服,在头发上打了摩丝,精心梳理了一番,然后拿了雨伞出门.走在雨中,我不时做着深呼吸,心情逐渐改观,连日来心头郁结的苦闷一扫而空,生活很美好我想,善待自己的人应该不要把烦恼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