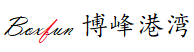说话的是一个秀美恬静的女孩,在等待我回答的时候她白净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我几乎可以从她的眼神中读出几许期待的神情,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充满了不争气的遗憾:"对不起,小姐,我想您认错人了。"
她的脸更加红了,在说对不起的时候她用的是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调,在她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周身笼罩在无边的罪恶感中好象我真地伤害了她,不过我的确不叫方伟。
电影已经开演了,我依然站在那里,无助地握着两张电影票。
我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变故,难道刘姨没有及时将她的安排通知给应该跟我共享这场电影的那位姑娘?又或者--我忽发奇想--是神通广大的老强找到了这位姑娘并向她讲明他们更需要我从而制止了这场无聊的游戏?算了,追本逐源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我自由了,我可以从容地奔赴老强的麻之约了,我轻松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在我正打算撕掉电影票,吹着口哨开路的时候,我看到了方才把我错认成别人的那个女孩儿。
她脸上的红晕业已褪尽,眼睛无神地瞥向路边的行人,一阵旋风卷着一团废纸滑过她纤细的足尖,撩动了她的长裙,我似乎能感觉到她在轻轻的颤抖.一个危险的念头象一条蛇一样滑过我的大脑,事后想起来,作出那个决定其实并没有占用我太多的时间。
我走了过去,"小姐,电影既然已经开演了,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说话时的镇定一如我日常在办公室向老周要烟,这一点令我自己都暗暗吃惊,同时我让她看见了我手中的两张电影票。
她诧异地睁大双眼,显然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却感觉长得如同一场办公例会。很快,她苍白的脸上又泛起我熟悉的红晕,我愉快地想,她或许已经弄清其实我不过是想帮她同时也是帮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而已.
"好吧,"她羞涩地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又补了一句,”谢谢你!”
她的笑很好看我想。
大概在电影放映到一半时,我腰间的蛐蛐开始不厌其烦地叫了起来,我眼前浮现出老强等人酒足饭饱后等我去埋单的凄惨景象,同时轻轻地掐断了蛐蛐的电源。
那天在电影院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奇怪的是我事后竟然对于那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没有一点印象。分手时,我们客气地互道再见,然后各奔东西。
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回家的路上我沮丧地想。
第二天,刘姨在电话里这样向我解释,人家姑娘忽然感冒发烧头痛恶心流鼻涕打喷嚏实在没法赴约,找我找不到又不知道怎么通知你,你等了一晚上吧?
"那是,一直到电影散场,这不是坑人吗?"我恶狠狠地说。
"别生气,别生气,也不能全怪人家,谁没个三灾六病午的,等姑娘病好了,我让她向你陪不是,还不成?"刘姨的口气好象那个姑娘是她自己的。
我其实根本懒得再见那个病罐子似的姑娘,只是缘于对刘姨多年的了解,知道此时拒绝无异于螳臂当车."随便,听您的."我的声调平淡得象在念文件。
挂断刘姨的电话,我急忙拨响了老强家的电话。
"你他妈活腻了吧?"老强的开场白和我预想的一字不差。
"是是,都是我不好,您老别动气,小心身体,我昨晚忽然病了…"在确实理亏的情况下,我的能屈能伸直追当年的韩信。
"得了得了,当我小孩那?"老强毕竟是老强,"少跟我来这套,泡妞去了吧?"
"您老真是神机妙算,也就是现在,要是您早生几百年……"我正欲逞三寸不烂之舌以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老强又一次无情地打断了我。
"行了哥们,打住,都是老中医了,这方子您就甭开了,我也不跟你废话,哥几个商量过了,这回不来顿大餐,难解哥们心头之气!"老强最让我心折的就是这股豪爽劲儿。
"地方你挑,时间你定!"我咬着后槽牙,坚定地说,脑中闪现出黄继光董存瑞等先驱的形象。
这是一个无聊的周末,老强的饭局约在了晚上。现在是中午,我想起了楼下似乎新开张了一家书店,于是决定去那儿消磨这一个下午。
书店铺面不大。店门外张贴着几张巨幅广告,一张上书某位名人留美归来痛下针砭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本书不容错过云云,还有一张是某位名女人抛开避忌袒露心扉爱情多舛命途多蹇宛如卢梭的<忏悔录>,我无心多看,信步踱入店内。
店内倒是清净,稀稀落落地只有三五个人。我随意浏览了一番,拣了一本沈从文的散文集慢慢翻看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有人在问:"可以帮我包装一下吗?要送人的。"
那声音轻轻掠过耳际,却如千斤重锤直捣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