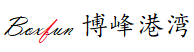"女的",老周向我绽出一个神秘的微笑,精心地把话筒递到我手里,似乎生怕惊到电话中的那位。
老周坐在我对面,他的办公桌跟我的紧紧对接--这是我所在的这家大机关办公室里最常见的一种布局--以便共用一部电话.鉴于资历上的巨大差异,老周理所当然的将电话机放在了他的那边,尽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我的电话次数远远多过他的以至无形中他仿佛成了我的接线员。
"谢谢!"我向老周回报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老周对于我的通话对象的性别总是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切,而对于这种似乎可以理解的关心我通常总会回报这样一种阐述着理解万岁的微笑,老周满意地低下头接着看他的报纸,两只耳朵却紧张地竖了起来。
"喂?您好!"我礼貌地向电话那端致意,"喂,是我",一个我熟稔的声音急匆匆地敲打着我的耳鼓,是刘丽--我应尊称为刘姨--一个我那遥远城市中的父母不知通过何种关系为我在这里找到的一门亲戚中的最热心的一员。
通常刘姨的电话不外乎三个内容,一是你的父母让某某人捎来了一些东西下班后你能来取一下吗,二是今天晚上家里炖了烧了煮了蒸了牛肉或猪肘或鸡腿你过来改善一下我看你最近好象瘦了,三是--最令我头痛的--我们同事认识的一个姑娘我看不错跟你挺配的我已经跟人说了让你见见……。
下班的高峰时间所形成的交通堵塞在这条长街上构造了数条蔚为壮观的钢铁长龙。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跌跌撞撞的前进,脑中飞速地盘算着如何尽快结束待会儿这场注定痛苦的见面。
刚才就要下班的时候,老强来了一个电话。老强是我的一个铁哥们,大学同学,家就在本市,最可贵的是他的父母长年驻扎在地球远端的某个小国,其结果就是老强的家基本上成为我们几个要好哥们的俱乐部。
"老余,小辉他们都来,三缺一,就等你了,几点到?"老强在电话中兴冲冲地问我,我支吾着无言以对。.
对于一个家在外地的单身男性来说,麻将起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你必须依靠它一圈圈地杀掉无数个难熬的苦闷夜晚,在每张牌的患得患失间暂时抛却尘世中无聊的喧嚣和争斗。我坦承我的确喜爱麻将,所以我无法拒绝老强的提议,但我的难处又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
我对哥们们隐瞒了所有刘姨安排的约会,这不单单是因为过低的成功率会有损我的颜面,同时也因为这种约会方式本身就是大学时卧谈会中经常被嘲讽的对象,而今天我更加觉得难以启齿。
"我要加会儿班,头吩咐的,没办法。八点我准到,宵夜我请,算是赔罪,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编排了一个缓兵之计。
"什么?大周末的,就你那点事,还用加班?"老强将信将疑,"你把我们哥几个晒在这儿,叫我们怎么办?挠墙啊?"
我哀求:"兄弟真是逼不得已,就饶过兄弟这一回,这样吧,你们先去吃饭,算我的?"老周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我也深深地为自己的奴颜媚骨汗颜。
所幸老强见好就收,"你丫快点,吃完饭你不到,以后就甭来了!"
刘姨安排的见面方式是这样的:在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的一座叫做长虹的电影院门口,我手持两张美国进口大片的电影票,等待一位身高约一米六五,留着披肩长发的女孩。
现在我已经将两张电影票攥在了手里,心里对如何及时脱身依旧不得要领!或许干脆在电影刚刚开始时假装腹泻进而溜之大吉?不行,太不仗义,而且没法向刘姨交待。要么直言相告,兄弟我另有要事恕不奉陪!会不会太伤人?或者……"你是方伟吗?"一个轻柔的女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
很不幸,今天的电话分明被导向了上述的第三个内容,寒暄过后,刘姨直切主题:"今天我们同事拿来一张姑娘的照片,我一看你猜怎么着(我不猜也知道会怎么着)还真不错,姑娘倍儿漂亮,听说人品也很不错,我已经替你答应见见了,怎么样,没问题吧?"
我本人对这种古老的媒人说合方式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我固执地以为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催生出爱情,尽管我知道我们的父执一辈的结合大多源于此,我依然不能对他产生任何一点好感。并且,仿佛为了证明我的观点似的,经刘姨介绍来的姑娘概莫能外地在一次见面后纷纷否定了第二次见面的可能性。这多少让我有点伤心却令人不解地极大鼓舞了刘姨的斗志,"德性!"通常在每一次惨痛经历后,刘姨总是这样及时总结和安慰我,宛如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愈挫愈奋的革命前辈一般,"咱还看不上她呢!别着急,下回刘姨再给你介绍更好的!"我真诚地感谢刘姨的热心,耐心和毅力并且实在难以拉下脸来拒绝刘姨殷殷的期盼,我知道她也负担着我父母的重托,于是只好一次又一次.. ….。
”时间,地点我已经都跟人家讲好了,你上点心,也老大不小了…”
下班的高峰时间所形成的交通堵塞在这条长街上构造了数条蔚为壮观的钢铁长龙。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跌跌撞撞的前进,脑中飞速地盘算着如何尽快结束待会儿这场注定痛苦的见面。
刚才就要下班的时候,老强来了一个电话。老强是我的一个铁哥们,大学同学,家就在本市,最可贵的是他的父母长年驻扎在地球远端的某个小国,其结果就是老强的家基本上成为我们几个要好哥们的俱乐部。
"老余,小辉他们都来,三缺一,就等你了,几点到?"老强在电话中兴冲冲地问我,我支吾着无言以对。.
对于一个家在外地的单身男性来说,麻将起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你必须依靠它一圈圈地杀掉无数个难熬的苦闷夜晚,在每张牌的患得患失间暂时抛却尘世中无聊的喧嚣和争斗。我坦承我的确喜爱麻将,所以我无法拒绝老强的提议,但我的难处又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
我对哥们们隐瞒了所有刘姨安排的约会,这不单单是因为过低的成功率会有损我的颜面,同时也因为这种约会方式本身就是大学时卧谈会中经常被嘲讽的对象,而今天我更加觉得难以启齿。
"我要加会儿班,头吩咐的,没办法。八点我准到,宵夜我请,算是赔罪,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编排了一个缓兵之计。
"什么?大周末的,就你那点事,还用加班?"老强将信将疑,"你把我们哥几个晒在这儿,叫我们怎么办?挠墙啊?"
我哀求:"兄弟真是逼不得已,就饶过兄弟这一回,这样吧,你们先去吃饭,算我的?"老周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我也深深地为自己的奴颜媚骨汗颜。
所幸老强见好就收,"你丫快点,吃完饭你不到,以后就甭来了!"
刘姨安排的见面方式是这样的:在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的一座叫做长虹的电影院门口,我手持两张美国进口大片的电影票,等待一位身高约一米六五,留着披肩长发的女孩。
现在我已经将两张电影票攥在了手里,心里对如何及时脱身依旧不得要领!或许干脆在电影刚刚开始时假装腹泻进而溜之大吉?不行,太不仗义,而且没法向刘姨交待。要么直言相告,兄弟我另有要事恕不奉陪!会不会太伤人?或者……"你是方伟吗?"一个轻柔的女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